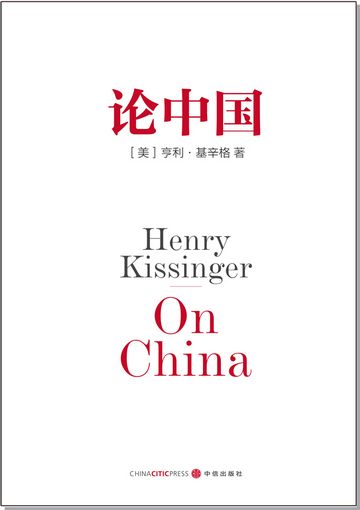
作者:【美】基辛格
译者: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基辛格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文化学者。他谈传统、谈历史,都是为了解决当下与将来中美交往中的问题,并提供一种外交思路。因此,他并未深入地分析中国传统的文化类型,也未对历史上的中美邦交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而只是作为历史现场中的目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将他捕捉到的信息进行重组,以资来者。
作为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亨利·基辛格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1971年,美国派出以他为首的秘密访华团,迈出了中美最高层交流非常关键的一步。在密访中国大陆四十年后,基辛格的新著《论中国》英文版由企鹅出版集团出版发行,《论中国》中文版的面世恰值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四十周年。《论中国》并非基辛格的中美外交亲历记或回忆录,作为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亲历者,基辛格愿意将自己参与其间的外交行为作为观察对象,他自己则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将中国作为美国未来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考察。
全书着墨最多的是中美如何从冷战环境下相互对抗甚至兵戎相见的敌对状态走向和解,如何为维护世界秩序、保障本国发展而积极合作的历程。这部分内容中的很多事件,基辛格都是历史的当事人,即便有些历史事件发生时他还未成为美国国家战略计划与外交事务的参与者,他作为观察者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在基辛格看来,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对立关系的形成与敌意逐渐消减的历史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为今日的决策者提供思路上的帮助。共和国建立时,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建立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美中新关系恰巧符合两国利益,朝鲜战争爆发,打乱了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才造成了共和国在外交上向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局面,事实上这只是为了与美国对抗才做出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共和国与苏联阵营存在根本的共同利益。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美中两国内部政治格局与东亚局势都发生了改变,两国才重回到艾奇逊所规划好的道路上。
如果当时在东亚不存在中美之外的强大势力,中美两国是否会走向和解?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审视中美关系的思路:在中美互不侵犯的前提下,假如东亚世界某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国家政局发生变化,并牵动中美国家利益的冲突,解决冲突的最好办法,要么是两国都不率先进行军事介入,要么是杜绝中美之外的任何强大力量介入其中,以免出现复杂的三角关系。
在书中,基辛格多次强调坚持“平等”与“务实”这两个原则的重要性。中美外交中,曾有过不平等与不务实的情况?
基辛格提出中国外交失误中本国传统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战略思维、制夷策略对古代中国的外交策略影响甚深,在外交方面,中国决策者既有以宗主国自许的傲慢,又有利用某一外邦作为牵制另一外邦的外交手腕,这些表现都是以儒家的等级秩序观念为基础的。一旦自身的实力不足以称雄,他们就会按照独特的战略观来经营势力,这种战略观是一种整体思维,并且强调在对峙中不求速胜、重视实力对比中渐变的作用。基辛格以18世纪末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在中国遭遇挫败事件为例,对清国以“天朝”自居而无视外交活动中的平等原则,以及在涉外谈判中更多从其宗藩体制出发而不求务实的情况进行了解析。
对外交事务极其敏锐的基辛格感觉到,共和国领袖们的身上依然部分存留着中国传统的制夷策略、战略思维与宗藩观念。这种描述不假,但不准确。毛泽东身上有中国传统决策者的特点,特别是其善于利用他国间的矛盾为共和国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几乎就是古代“以夷制夷”的现代翻版;他对亚洲格局的设想,也颇有重建宗藩体制的意味。不过,从邓小平开始,情况出现了变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最高决策者的神秘色彩在邓身上仍有体现,但在外交场合,他能够坚持平等原则,注重务实,而这种外交态度也被之后的共和国决策者所继承。
基辛格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文化学者。他谈传统、谈历史,都是为了解决当下与将来中美交往中的问题,并提供一种外交思路。因此,他并未深入地分析中国传统的文化类型,也未对历史上的中美邦交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而只是作为历史现场中的目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将他捕捉到的信息进行重组,以资来者。
他十分关注“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外交角度,他看到共和国谨慎地强调“和平崛起”对东亚与世界的益处,并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和平的态度;在具体外交事件中,维护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使共和国不时表露出强硬姿态。同时,他也注意到在共和国内部呼吁在亚洲乃至世界确立强势地位的思潮。基于各种现象,他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强大后,中美在亚洲是否会有不可调和的冲突?
一战发生前,英德两国在欧洲大陆的利益出现冲突时,英国外交家艾尔·克劳提交给政府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指出,基于国家利益的结构性冲突必将导致英德矛盾的不可调和。
基辛格强调,如果将国家利益的摩擦视为不可调和,冲突就在所难免,那只会出现零和博弈,即最终依然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如果承认摩擦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外交努力进行策略上的调整,使摩擦控制在两国都能接受的范围,就会维持和平局面。
在他看来,能否避免克劳所预言的结果,主要在于两国能否将中国崛起过程中出现的利益摩擦视为可以解决的问题。他承认,随着共和国的强大,中美之间在国家利益上必然会出现摩擦,不同的体制与国家治理方式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放大这种摩擦。
他还注意到“崛起”背景下共和国内部的某些舆情,如《中国梦》和《中国不高兴》等所反映的国家观与对美情绪,特别是这种情绪中反映出的零和博弈思维与克劳备忘录的共同点。对此,他一方面表示了对这种看法未被政府采纳的庆幸,另一方面也不无忧虑。他的庆幸与忧虑,都带有一种美国式的天真,他对共和国内部出现的思潮理解有些简单化,而且出现了误读。在中国大陆,要求政府在对外事务上立场强硬的呼声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曾有过爆发,当时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搅动了民族主义情绪,而《中国不高兴》只不过是在新时期下步前者之后尘。这两部相隔十年的畅销书,都不过是为经济利益而煽动、取悦受众的劣作,而其受众对“说不”、“不高兴”的呼应更多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对国家外交政策并无有效影响。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中美间历次大事件中,共和国内部民族主义的高涨与国家的处理策略之间的关系,例如1999年轰炸共和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美国女演员莎朗·斯通的“报应”言论事件等,而这些才是真正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网络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