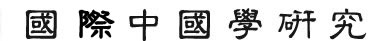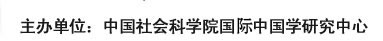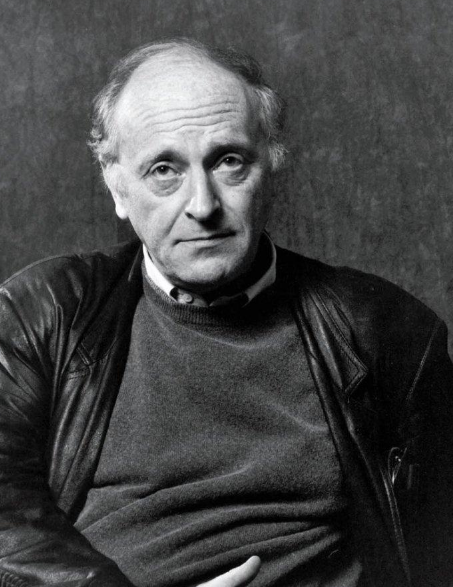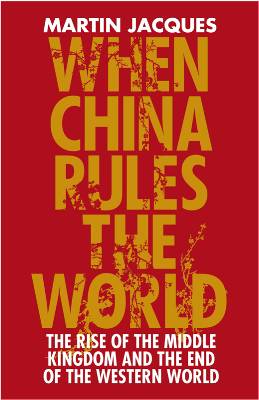作者:唐磊
一、学科与学科化过程的一般理论
关于学科(discipline)这一舶来概念,西方学者给出过林林总总的意见。较为符合本文理论框架设定的一个定义出自《社会与行为科学国际百科全书》,该条目的撰写者德国学者鲁道夫·施蒂希韦(Rudolf Stichweh)提出:“学科作为科学内部不同部类的基本单元划分是十九世纪的产物。拉丁语disciplina,意谓教导,早就是学校和大学出于教学目的进行知识组织时所使用的一个术语,但直到19世纪才真正建立起学科交流的体系。从那时起,学科开始在科学的社会体系中起着一整套结构构架的作用,而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则作为学校教学的一个主题领域,最终则指向职业角色的安排。尽管科学领域的分化过程一直在进行,但学科作为一套基本的结构构架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上述功能方面保持着稳定。” 其实“discipline”的拉丁文源头不仅有“disciplina”,还有“discipulus”,指教导的对象,由此发展出在“discipline”现代的两重主要词义,即“学科”和“规训”,这也恰恰反映出学科不仅是一套知识的分类体系同时也是具有约束力和引导力的社会建制的双重特点。
按照西方学者的一般意见,从认知的角度,学科需要具有如下一些要素。首先,学科要有独立的研究领域,由于自身边界的存在,我们才能勾勒出现代学科的地缘版图;其次,关于该学科研究对象的专门知识得以积累,这些专门知识并为其他学科所普遍共享;第三,学科有自己独特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第四,学科自洽于研究对象的陈述方式;第五,发展出一套与学科特殊需求相呼应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另外,从社会建制方面来考察,学科的制度化过程往往产生一些明显的指征。例如,相对稳定的学科研究人群,即专业团体,进而发展出依托于专门协会、学会等形式而存在的学术共同体;拥有学科展示自身成果和取得话语地位的阵地,最主要的是刊物和定期会议;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取得专门的建制地位,比如在大学中有专门的教席岗位,有专门的课程科目及学位,最成熟的形式是发展出专门的院系。
上述种种,都是学科获得固定“身份”的重要指标。换句话说,栖身某一学科的研究者对该学科和自身作为学科研究者的身份认同,主要取决于上述指标的完满程度。
二、“汉学”、“中国学”学科的成立及其背景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汉学”(Sinology),也始自学科“自主性”(autonomy)彰显的十九世纪。雷慕莎(Jean Pierre-Abel Remusat,1788-1832)是促进汉学学科建制化的关键人物,他不仅于法兰西学院首开汉学讲席,还与同道创立了亚洲协会,并创办了专业期刊《亚洲学报》;而中国学(China Studies)则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走向学科独立,则呼应了学术发展史上的另一场现代化浪潮,即二战之后兴起的、以美国为主导(以美国范式为主要范式)的社会科学的勃兴。社会科学在二战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并非某种理论(诸如凯恩斯主义或结构—功能理论)或某种方法(诸如田野调查或定量分析)被提高到显著地位,而在于“战后的社会科学被铸成综合系统的理论”。成长于美国的“中国学”不同于成长于欧洲的“汉学”,除却研究对象(不同内涵的“中国”)所发生的明显变化之外,更深刻的区别正在于美式社会科学的高度综合性。对此,中国学重要创立者之一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就有过很好的总结,他在1968年美国历史年会上演讲时说:“作为思维方式来观察,历史、社会科学和包括汉学在内的地区研究目前已交融渗透。它们不再分属彼此无关的知识渠道。我们在研究一门学科时不可能不涉及其他。”
由此可见,汉学和中国学在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成立均与近代以来的学术现代化过程有莫大干系。汉学和中国学所涉主题和领域甚夥,在智识层面上很难总结出学科内部可普遍共享的范式或理论,但透过其融入学术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仍可以寻绎它们有别于传统学术的智识特点。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从汉学到(美式)中国学的转关不仅仅出于学术发展自身的动力,它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和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费正清就曾道破这一层,而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说得更明白:“人们把当代中国学研究划为一个孤立的领域,这反映了把共产党的历史与前共产党的历史从根本上截然分开的概念,仿佛要体现1949年的戏剧性决裂,就要有一种崭新的、与纯汉学研究相反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
三、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化过程——简要的描述
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是对海外汉学/中国学智识成果及知识生产过程及其与社会、文化诸因素互动过程的再研究。它最初以介绍和简要的学术史梳理形态出现,发生于中国学术始与现代学术全面接轨的民国时期,而真正集中的发展则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关于其总体的发展史,已有较多概括,在此不拟展开。
在西方学术界,汉学和中国学产生于不同时代,有各自相对明确的内涵,总体的范式也有明显区别;相比而言,与它们分别对应的“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则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术共同体上多有交叠。有许多现象可以作为说明。例如,海外汉学研究的刊物或学术会议并不排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文章,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也会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课题,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专门学者融于共同的专业协会(比如“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协会”)。又比如,李学勤在2000年的“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一文中提出:“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关注的六大问题,包括“汉学如何起源,迄今走过了怎样的发展道路”、“汉学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语言等等方面已经作出了哪些研究”、“汉学家及其著作是在怎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国际汉学对中国学术的演变发展起过什么样的影响”、“汉学对西方学术的演变发展又有着怎样的作用”、“国际汉学的现状以及在新世纪中汉学进展的趋势”,稍加概括,大概可以分为对汉学的学术情报研究、学术史研究(回顾与前瞻)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思想史、知识社会史研究;这完全可以适用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基本内容和方法的概括。
在学科建制化方面,二者经过三十余年发展,均具备了若干“学科化”的明显标志,比如固定建制的研究机构(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有影响的专业期刊(《国际汉学》、《世界汉学》等)、专门的学科和学位(从最早北京大学于1985年开始招收海外中国学研究硕士生到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此类学科点和学位点),等等。从建制层面看,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性已比较完备,称它们为学科也不是没有理由。
对学科文化有深入研究的英国学者托尼·比彻等人指出:“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相关系科的存在来确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系科都代表一门学科。一门学科是否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即学术可靠性、知识的主旨和内容的恰当性等一套概念,尽管对它们没有严格的界定,但却是约定俗成的。”如果把专门的系科作为学科成立的一个必要指标,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学科独立性还不完备,目前国内只有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是以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教学为主业。如果再究之以对学科智识属性的认可这一更高标准,恐怕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学科独立性就令人难以接受。也就是说,二者在学科化方面尚不具有完全的自足性,称之为中国学术界正在形成和可能形成的新兴学科大概更符合事实。
四、从文献计量结果看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发展
不过,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国外中国学研究室的建立为起点,中国学术界在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领域的积累已有将近四十年的历程。无论它们是否会成长为中国自身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学科,我们仍然可以考察通过学术知识生产的累积,二者是否以及如何向着学科化的方向发展。至少,我们可以探索在学者队伍、学术平台、学术范式等方面的发展线索和特征,并且比较海外汉学研究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在上述方面的共性和差异。
为此目的,我们对1979-2013年收录于CNKI文献库中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按照主题关键词进行了检索,分别获得1811篇(汉学)和1141(中国学)条数据,并对其进行标引和计量分析,最终形成如下一些初步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采用的检索策略并不保证能检索到这段时间内大陆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全部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文章,许多文章因为在题名或关键词中不包含“汉学”或“中国学”而被排除在外。
1. 从历年发文数看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发展
|
我们根据1979-2013年历年发文数量绘制了折线图(图1.1和1.2),用以显示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文章数量(含期刊文章、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的增长情况。
图1.1 1979-2013年海外汉学研究文章数量统计 |
|
|
|
图1.2 1979-2013年海外中国学研究文章数量统计 |
|
|
显然,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经历相似的发展阶段,阶段特征也基本相同,即21世纪之前稳步发展,进入21世纪大步前进。总体来看,历年海外汉学研究的期刊文章多于海外中国学研究发文总数(1577:1041),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数量也是如此。这说明,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和研究参与要高于海外中国学。
但从总体规模来看,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二者都不算“太火”。2013年两个领域发文数量分别为208篇和106篇。笔者随手做了一个比较,用“国学”做主题词,仅2013年就检得超过7000篇(数据清洗前的结果),大概是1979-2013年以“中国学”为主题词所得文献总和(数据清洗前为接近3500条)的两倍。因此,从发文规模看,海外中国学和海外汉学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 主要发文机构与支持基金的统计与分析
1979-2013年间,发表过海外汉学研究文章的机构共有774个,其中,发文量为1篇的有627个,占比81%,接近94%的机构发文不超过3篇。这似乎说明,绝大多数机构学者从事该领域研究只是偶一为之的事情。发文量在前十位左右的机构按发文量达到9篇计算有11家(占全部机构数的1.4%),它们的发文数占全部发文数的比例为8.5%。排名第一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排名二三位的分别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如果不细分到二级机构,则北京外国语大学居于榜首(79篇,含所属各二级机构,下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依次二三位(59和56篇)。
表1.1 海外汉学研究主要发文机构列表
|
排名 |
机构名称 |
发文数 |
|
1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
34 |
|
2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
32 |
|
3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 |
14 |
|
4 |
国家图书馆 |
13 |
|
5 |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
12 |
|
6 |
北京大学历史系 |
9 |
|
6 |
华东师范大学 |
9 |
|
6 |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9 |
|
9 |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
8 |
|
9 |
北京大学中文系 |
8 |
|
9 |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
8 |
|
12 |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
7 |
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发文机构众多且大多为“偶一为之”的现象也存在。1979-2013年间涉及的发文机构共有543家,其中,发文量为1篇的有436家,占比80.3%,接近95%的机构发文数不超过3篇。发文量较多(7篇及以上)的机构有12家(占比2.2%),其发文总数占全部发文数的比例为14.3%。主要机构发文的集中程度略微高于海外汉学研究领域。发文前三甲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该校社会科学部。如果不细分到二级机构,则华东师范大学(77篇)超越中国社会科学院(72篇)排名第一,北京大学(41篇)居于第三。
表1.2 海外中国学研究主要发文机构列表
|
排名 |
机构名称 |
发文数 |
|
1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
34 |
|
2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
32 |
|
3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 |
14 |
|
4 |
国家图书馆 |
13 |
|
5 |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
12 |
|
6 |
北京大学历史系 |
9 |
|
6 |
华东师范大学 |
9 |
|
6 |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9 |
|
9 |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
8 |
|
9 |
北京大学中文系 |
8 |
|
9 |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
8 |
|
12 |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
7 |
按照地域来看,从事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主要机构基本分布在北京和华东两地,尤以北京居多。进一步分析近三年的数据发现,这一趋势近来没有明显变化,北京仍然是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生产区域。
另外,我们对基金资助来源做了简要的考察,发现有21种基金资助了海外汉学研究,有13种资助了海外中国学研究。在两个领域,国家社科基金都是最大的资助方,在其资助下出产的论文数均超过了由其他基金资助所出产论文数量的总和。
3. 主要发文期刊平台的统计与分析
1979-2013年间,发表过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期刊分别为632种和411种。这些期刊基本上都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大类期刊。由于存在期刊更名、停刊等情况,我们无法精确计算所涉期刊占全部人文社科类期刊的比例。但有一个基数可以作为参考:2014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第一批认定的学术期刊5756种,其中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为2043种。据此估算,在中国大陆发行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中,分别有约三成和两成的刊物发表过海外汉学研究以及海外中国学研究方面的文章。
表2列出了发文量排名前十(含并列)的刊物,它们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权威期刊”或“核心期刊”,唯一例外的《博览群书》也是在知识界、思想界有较大影响力的期刊。其中,《国外社会科学》和《国际汉学》分别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最主要的发文阵地。同时,《国际汉学》也是海外中国学研究第二大发文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像《国际汉学》、《世界汉学》这样的专业对口期刊外,一些传统上偏于人文学科的刊物如《中国文化研究》、《读书》、《中国史研究动态》和《中国图书评论》等,体现出对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兼收并蓄”。不仅如此,文史类刊物尤其是史学类刊物在主要发文刊物中有较大比重,在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尤其如此,这可能说明海外中国学研究具有侧重学术史进路的特点。
表2 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主要发文刊物统计
|
海外汉学研究主要发文刊物 |
发文数 |
海外中国学研究主要发文刊物 |
发文数 |
|
《国际汉学》 |
148 |
《国外社会科学》 |
115 |
|
《中国文化研究》 |
45 |
《国际汉学》 |
53 |
|
《国外社会科学》 |
42 |
《读书》 |
24 |
|
《世界汉学》 |
41 |
《中国史研究动态》 |
19 |
|
《读书》 |
33 |
《世界汉学》 |
14 |
|
《中国史研究动态》 |
15 |
《当代中国史研究》 |
14 |
|
《中国图书评论》 |
15 |
《历史教学问题》 |
13 |
|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
14 |
《中国图书评论》 |
11 |
|
《中国比较文学》 |
12 |
《中国文化研究》 |
10 |
|
《博览群书》 |
11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
10 |
|
《文史哲》 |
11 |
《史学理论研究》 |
10 |
|
《文学遗产》 |
11 |
《史林》 |
10 |
|
《江西社会科学》 |
11 |
《探索与争鸣》 |
10 |
|
总计 |
409 |
总计 |
313 |
|
在全部期刊发文的占比 |
25.9%(1577) |
在全部期刊发文的占比 |
30.1%(1041) |
4. 高产作者群体及其分析
海外汉学研究1811篇文献涉及作者1398位(人均约1.3篇),而海外中国学研究1411篇文献共涉及作者961位(人均约1.2 篇)。我们采用文献计量学中的“普赖斯定律”来确定所谓的“高产”作者,该定律认为,撰写全部论文一半的高产作者的数量,约等于全部科学作者的平方根(分别是37.4和31),据此,两个领域的计算结果都是,发文4篇以上的作者算作高产作者,他们(分别是43位和40位)组成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如表3.1、表3.2所示)。
表3.1 海外汉学研究高产作者统计表
|
姓名 |
发文数 |
姓名 |
发文数 |
姓名 |
发文数 |
|
张西平 |
32 |
李新德 |
6 |
孟庆波 |
4 |
|
李明滨 |
13 |
钱婉约 |
6 |
张杰 |
4 |
|
李雪涛 |
12 |
马军 |
6 |
徐强 |
4 |
|
阎国栋 |
11 |
刘彩艳, 孟庆波 |
5 |
朱仁夫 |
4 |
|
顾钧 |
10 |
李真 |
5 |
李学勤 |
4 |
|
任大援 |
9 |
王海龙 |
5 |
李明 |
4 |
|
阎纯德 |
9 |
钱林森 |
5 |
杨惠玉 |
4 |
|
柳若梅 |
8 |
陈倩 |
5 |
段洁滨 |
4 |
|
程章灿 |
8 |
任增强 |
4 |
董海樱 |
4 |
|
乐黛云 |
7 |
刘东 |
4 |
谭树林 |
4 |
|
仇华飞 |
7 |
刘丽霞 |
4 |
郑天星 |
4 |
|
吴原元 |
7 |
叶农 |
4 |
陈珏 |
4 |
|
李逸津 |
7 |
吴涛 |
4 |
陈金鹏 |
4 |
|
蒋向艳 |
7 |
吴贺 |
4 |
|
|
|
顾明栋 |
7 |
周发祥 |
4 |
|
|
表3.2 海外中国学研究高产作者统计表
|
姓名 |
发文数 |
姓名 |
发文数 |
姓名 |
发文数 |
|
朱政惠 |
26 |
曹景文 |
6 |
周阅 |
4 |
|
吴原元 |
15 |
阎纯德 |
6 |
孙歌 |
4 |
|
张西平 |
14 |
顾钧 |
6 |
彭传勇 |
4 |
|
何培忠 |
10 |
任大援 |
5 |
李学勤 |
4 |
|
钱婉约 |
9 |
吕杰 |
5 |
杨静林 |
4 |
|
石之瑜 |
8 |
孟庆波 |
5 |
王晴佳 |
4 |
|
梁怡 |
7 |
张注洪 |
5 |
白云飞 |
4 |
|
王祖望 |
7 |
段洁滨 |
5 |
钱宏鸣 |
4 |
|
韦磊 |
7 |
黄育馥 |
5 |
阎国栋 |
4 |
|
严绍璗 |
6 |
刘彩艳 |
4 |
陈倩 |
4 |
|
仇华飞 |
6 |
刘招成 |
4 |
顾明栋 |
4 |
|
侯且岸 |
6 |
卢睿蓉 |
4 |
黄定天 |
4 |
|
崔玉军 |
6 |
叶坦 |
4 |
|
|
|
徐浩然 |
6 |
周武 |
4 |
|
|
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发文量排在前十位的学者其学术背景无一例外地出自传统文史学科,这一现象多少显示了海外汉学研究对于学者知识储备的要求和他们的学术路径依赖。其中,有几位学者如任大援、程章灿和乐黛云,他们的主要研究方向并非海外汉学研究,而只是兴趣使然的“兼治”。相比之下,在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学者,基本上都以该领域为主业或至少是主业之一,像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主治政治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王祖望(中国社科院情报所,主治社会学和社科情报研究)这样的学者其学术领域则有明显的跨界性。另外,其中不少学者是以海外中国学的学术史研究见长,而这一领域本身就具有跨学科性,因此,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高产的作者,其学术研究都具有一定的跨学科色彩。或许还可以说,他们在学术界的被认可也更能够不依赖于传统的文史政社一类学科,而是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共同体内确立自身的被认同和地位。当然,由于学科属性和边界的相对模糊,要取得它们的风险与代价也可能更高。
5. 从研究文献关键词看学科研究热点及学科独立性
CNKI提供的每篇文献均标注有主题词和关键词等元数据信息,我们将其中关键词信息抓取下来,然后将关键词及其出现频次通过在线词云软件WordItOut生成关键词云,如图2.1和2.2所示。海外汉学研究领域1811篇文献共有6257个关键词,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1141篇文献共有4222个关键词,图中所示的关键词是出现频次较高的那一些。
(1)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存在相互认同和定位交叉。在海外汉学研究文献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除“汉学研究”和“汉学”外,排在第三位的就是“中国学”,而在海外中国学研究文献中,紧接着出现频次最高的“中国学”的就是“汉学研究”。并且,两个领域拥有不少共同的高频关键词。另外,海外中国学研究更能容纳海外汉学研究而不是相反,这一点从前者的高频关键词中包括了传统海外汉学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而后者鲜有关于现当代中国和社会科学范畴的关键词可以窥见。
(2)从关键词出现频次看,美国、法国和日本的汉学/中国学受关注度较高,被研究较多的海外汉学/中国学家也主要来自这几个国家。
(3)海外汉学研究领域,传教士(耶稣会士)汉学、中西文化交流、现代文学、汉语教学与传播是较受关注的议题,而在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除了包纳着海外汉学研究的主要热门领域外,也有像近现代史、毛泽东研究这样更符合“美国式中国学”范畴的对象领域。
(4)海外汉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前十位“汉学家”是伯希和、戴密微、理雅各、费正清、顾彬、利玛窦、阿列克谢耶夫、沙畹、宇文所安和高本汉;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十位“中国学家”是费正清、史华慈、伯希和、拉铁摩尔、戴密微、沙畹、列文森和沟口雄三。总体上,我们从这里看到了“汉学”和“中国学”比较的明显分殊,同样也看到了“中国学家”更大的包容性或者说不明确性。此外,从他们的国籍看,也能看出汉学与中国学各自不同的代表性学术传统,分别来自欧洲尤其是法国和美国。
6. 所涉国家的频次统计与分析
我们对每篇文献所涉的国家也进行了人工标引,如对史华慈及其学术的研究则标为“美国”,对于涉及多个国家的每个国家都算被涉及一次,而如果是讨论海外汉学研究学科性或学科发展一类的文章则归为“中国”。以此得出的统计结果通过世界热力图方式予以直观呈现,如图3.1和3.2所示。
图3.1 海外汉学研究所涉对象国家的频次分布
图3.2 海外中国学研究所涉对象国家的频次分布
统计数据表明,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最频繁被涉及的国家依次是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日本。尽管涉及美国的文章数量最多(330篇),但是涉及德、法、英等欧洲国家的文献数量(不算排名较多的俄罗斯)总数(约650篇)要远超美国。在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依然是涉及美国的最多(298篇),其后依次是日本和俄罗斯,其数量约为涉美国篇数的一半和三分之一,涉及欧洲诸国的文献总量(250篇左右)仍不及涉美国文献量。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学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欧洲,其次是美国,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美国。
7. 对海外汉学/海外中国研究的研究层次与进路的分析
前面提到过,海外汉学研究/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研究路数包括三种,即学术情报研究、学术史研究(回顾与前瞻)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思想史、知识社会史研究。我们对海外汉学研究1811篇文献和海外中国学研究1141篇文献按如下的分类方式(基于研究方法)做了最粗类别(粒度)的标引,目的是检查这两个领域总体研究层次处于何种水平。需要说明的是,述评(基本属于学术情报研究层次)和研究之间并无截然清晰的区分标准,我们的区分标准大体上遵照着原创性、思想性程度的原则,但事实上学问一事本来就是基于前人、踵事增华,评议、漫谈之类的文体也不见得限制思想发挥,因此这里的区分很难说完全严格执行了某一种科学严谨的标准,只能是为了实现分析而努力按照一贯的标准来进行标引聚类。最终结果如表4所示,加上时间维度后如图4.1和4.2所示。
|
分类 |
收录标准 |
|
研究 |
对海外汉学/中国学方法论的总结和探讨、从学术史、思想史角度的发生学和接受史等考察、对海外中国学/汉学的反思和启示,对概念和问题的辨析、对中国学/汉学家观点的批评和回应 |
|
述评 |
述评、述论、概述、漫谈、展望、书评(含序跋)、评介、会议主旨发言、会议综述或纪要 |
|
翻译 |
翻译发表的域外学人有关具体问题的中国/汉学研究成果 |
|
访谈/对话 |
与域外学人进行的访谈和对话,或针对中国学/汉学研究展开的对话 |
|
简介/消息 |
机构、人物与新书的简介、会议消息等信息量不大的介绍性短文 |
表4 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方法及运用次数统计
|
海外中国学研究方法 |
海外汉学研究方法 |
||
|
研究方法 |
发文数量 |
研究方法 |
发文数量 |
|
述评 |
637 |
述评 |
942 |
|
研究 |
373 |
研究 |
682 |
|
简介/消息 |
92 |
简介/消息 |
118 |
|
访谈 |
25 |
访谈/对话 |
55 |
|
翻译 |
14 |
翻译 |
14 |
|
总计 |
1141 |
总计 |
1811 |
在研究类文献中,由于很难找到可以足够收敛的聚类方式,能够设想到的标准(比如研究主题、具体方法)都可能由于难以判断边界而无法明确分类,或是导致分类过细而失去统计分析上的意义,故而我们没有做出进一步的细分。但在清理数据的过程中,我们也直观到一些比较显著的现象,足以说明某些问题。显然,在两个领域中,学术情报研究层次的述评都是主要的研究方式,但还达不到库恩意义上的“范式”,因为即使文献综述已经有成熟的规范和要求,那也是面向所有学科的,也没有观察到一套独属于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特殊的综述体式/规范。因此,我们只能说,综述、述评形式的学术情报研究仍然是两个领域的最主要进路。
首先,研究类文献大多采取学术史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思想史、知识社会史研究的进路,其中,知识社会史或学术思想史又少于一般性的学术史研究。这大概是因为,前者的对研究者本人的综合素养要求更高。通过对海外之学的研究和对话来反省、提升对本国问题思考的文章则更是少之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其次,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类文章生产数量大幅提高,但其中大量增加的是有关两个领域学科性、学科定位的研究和反思文章,粗略统计,这类文章的增长量几乎与前面所说的几种学术史研究类文章的增长量相当。这一方面说明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学科自主意识在增强,自然就表现为对学科内涵、关于学科的种种身份属性(诸如研究对象、方法论/研究范式)的讨论在增多,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现象也体现出学术界尤其是主要从事这两个领域研究们的学者们(因为这类文章也主要是他们撰写的)对自身领域学科化的期待,以及他们对这两个领域学科独立性的焦虑。如果将这类文章剔分出来放在一起,仅看标题就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再者,进入21世纪后,研究类文献中还有一类文章的增长显得突出,即有关汉学的“殖民性”和中国自身学术话语地位的探讨文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围绕有关“汉学主义”、“中华学”的文章,前者在过去几年里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后者也曾在2000年前后一度被炒作。这两个例子尽管看似在问题意识和价值关切上没有太多关联,但都可以视作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学科化进程的危机呈现与自我解构。“汉学主义”通过对西方汉学话语背后的政治性(殖民性)的拷问对汉学以及国内的海外汉学研究的合法性产生冲击,“中华学”希望通过为本土的中国研究注入某种民族主义精神来对抗海外中国学的话语霸权,其“批判—建构”的过程也是将海外“中国学”赋予过多政治意味来完成的。此类文章的出现并累积出一定量级,说明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要实现学科化不仅需要确立起学科建制、研究范式等,还需要凝定出自身的价值关怀以及通往这种关怀的心智路线。
五、进一步的讨论
以上我们基于CNKI数据库中主题词为“汉学”和“中国学”的1811和1141篇文献,以文献计量的结果做了简要的分析,并用“学科化”的视角做了一定的阐发。关于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两个领域是否将发展为独立的学科,笔者还有些许不成熟的思考,放在本文最末,希望能为从事这两个领域研究者们进一步思考和行动提供些许参考。
首先,平心而论,海外汉学和海外中国学本身就是包容性很广的领域,其在海外学术界的学科化程度也因不同地域背景和现实处境而有不同,中国本土对它们的再研究是否能够从一门学问上升到一个学科也不是应然之事,更多的时候,相关的期冀和努力最终更多地成为争取学术资源的途径和手段。
其次,应当看到,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不断面临各种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可能来自于,固有学科内学者以自身学科背景为支撑和外语、信息获取能力为保障来从事相关研究时所体现出的优势。美国著名中国学家魏昂德曾指出,“中国研究这一领域依然存在,而且其繁荣程度前所未有,但是目前正在面临挑战,在某些方面被学科内的中国研究所取代。”这种现象也正发生在我国的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领域。因此,以这两个领域为主攻方向的研究者需要从研究范式、内在价值等方面确立不同于专业学科进路的独特品质。
再者,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除了因为争取资源的关系来发展自身的学科性外,终究更多表现出的是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如何立足于跨学科性来发展出自己的独立空间也许更值得思考。对此,本领域的当代先行者孙越生先生曾指出,无论中外的中国学,都应该以“在中国研究的核心课题上开展新的综合”为高标。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2013年辞世的朱政惠先生也提出:“海外中国学的外延很广,举凡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军事等,都在其研究范围之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难以穷尽,只能通过具体学科的研究来各个击破。它们的研究会有交叉重叠,但又相对独立。海外中国学研究需要相关学科的方法论的借鉴,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很多经验,也会成为相关学科建设的有益养分,即使是谬误也会是一种借鉴。几十年的努力已使学者形成这样的研究工作愿景: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学科群的建设,是学科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当各个学科背景下的研究都深化了,全局意义上的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群大厦也会矗立起来。”“高度综合”之说,确实能够激发出无穷的智识挑战欲,但如何综合还需要学者们不懈的探索。
最后,我认为,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者其实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纲领,用通俗的话讲,无非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换句话说,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要以提升中国本土的中国研究为宗旨,即以对海外之学的研究来鞭策、启迪、丰富、提升本土之学,以中外学问的相互砥砺来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对前途的把握。这样一种“道问学”本来就是海外汉学/中国学领域得以发生和发展的缘起和动力,也是它们展现自身价值和魅力的根本途径。(原载《国际汉学》2016年第3期)
上一篇:缺席的中国